|
|
#1 |
|
注册用户
注册日期: Apr 2001
来自: shanghai
帖子: 6,394
精华: 1
|
请大家看看关于司马翎的一篇文章
请大家看看关于司马翎的一篇文章
蒙塵的明珠--司馬翎的武俠小說 【提要】 司馬翎是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上值得重視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節奏舒徐沉穩,復又充滿智性的內涵,因此,曾搏得許多舊讀者的喜愛。近十幾年來,由於時代節奏迅快,司馬翎穩健的風格逐漸少人問津,且在金庸盛名的影響下,更少有人願為之推介,以至如同一顆蒙塵的明珠,亟待識者為其拂垢揚塵。 司馬翎的作品以穩健與理性的架構取勝,推理縝密,在武俠小說中別出一格,無論是在人物的刻畫和情節的布局上,皆處處呈顯出智性的閱讀效果。司馬翎擅長以其廣博而精深的雜學,在武俠小說中設計新穎而不失其合理的武功,同時透過武功的設計,展現了他對人性和道德的關懷。 更重要的是,司馬翎的江湖世界中,女俠不再只是瓶花的附庸角色。 司馬翎往往不吝於讓其小說中的俠女展露其豐富而深刻的內心世界,情感自主,女性的智慧備受強調,可以說是武俠小說中唯一能讓女性發展出個人生命境界的作家。 【關鍵詞】 武俠小說 司馬翎 推理結構 武藝文學化 雜學 女俠 女智 武俠小說是臺灣通俗小說的主流,幾十年來,以其精采迭見、豐富曲折的情節,委婉細膩、深刻入微的人性刻劃,風靡過無慮百萬計的讀者。據估計,在此期間,至少有四百位的作家投入武俠創作的行列,而創造了逾四千部以上的作品 ,可謂名家輩出,各領風騷。 縱觀臺灣武俠小說的發展,凡經四變,早期的先驅作家,衍傳著民國初年諸大家的餘烈,如郎紅浣(1952年的《古瑟哀絃》)之取法王度廬,以「英雄兒女的悲歡離合」為主線 ;成鐵吾(1956年的《呂四娘別傳》)之與蹄風同步 ,雜揉民間傳奇與歷史題材,寫清宮舊事,屬草萊初闢之創始期。其後,臥龍生(1957年的《風塵俠影》)以宏偉的結構、精巧的布局崛起;司馬翎(1958年的《關洛風雲錄》)以縝密的思致、嚴謹的推理見長;諸葛青雲(1958年的《墨劍雙英》)以斯文的雅緻、纏綿的情致取勝,鼎足而三;其他如伴霞樓主(1958年的《鳳舞鸞翔》)之精警生動、古龍(1960年的《蒼穹神劍》)之初試啼聲、上官鼎(1960年的《劍毒梅香》)之新穎出奇、蕭逸(1960年的《鐵雁霜翎》)之新藝俠情、東方玉(1961年的《縱鶴擒龍》)之變化莫測、柳殘陽(1961年的《玉面修羅》)之鐵血江湖,亦皆繽紛可觀,於傳衍民初諸家外,復能漸開新局,屬發展時期。1961年以後,上述諸家,銳意興革,迭有佳作,陸魚於1961年作《少年行》、司馬翎於1962年作《聖劍飛霜》、古龍於1964年作《浣花洗劍錄》,開啟了「新派」武俠小說的紀元,並且為後來為期十年以上的「古龍世紀」鋪奠了深厚的根基,是為鼎盛時期。1977年以後,雖有溫瑞安之《四大名捕會京師》廣獲矚目,古龍亦仍不時有新作誕生,然多數作家皆漸告引退,武俠小說寖漸步入衰微;1978年,金庸小說解禁,以「舊作變新說」,造成至今仍影響深遠的「金庸旋風」,更使名家卻步;1980年,李涼以《奇神楊小邪》始作俑,引領出一批批標榜著「香豔刺激」的「偽武俠」充斥坊間,武俠小說幾乎到達不堪聞問的地步,是為衰微期。 在此「四變」的武俠小說發展期間,號稱「臺灣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古龍的成就最為可觀,其中司馬翎(1933~1989)的地位更屬重要,因為他的創作時期跨越兩期,風格三變,頗足以視為一個縱觀武俠小說發展歷史的縮影。 司馬翎本名吳思明,廣東汕頭市人,1957年自香港負笈來臺,就讀於政治大學政治系,於大二時(1958)以《關洛風雲錄》一舉成名,截至1985年《聯合報》連載未完的《飛羽天關》止,廿多年來,完成了三十多部的作品,其間三易筆名:1960年以前,以「吳樓居士」為名,發表了《關洛風雲錄》、《劍氣千幻錄》、《劍神傳》、《仙洲劍影》、《八表雄風》等作;1961年,改用「司馬翎」名義,發表了《聖劍飛霜》、《掛劍懸情記》、《纖手御龍》、《帝疆爭雄記》、《劍海鷹揚》、《人在江湖》等大多數成名作;1970年,因故一度輟筆,偶有所作,則以「天心月」為名,在香港報刊登載了《強人》、《極限》諸小品;1980年後,拾筆欲重回江湖,復因病魔纏身,無法專力投入,僅有《飛羽天關》(未完)、《飄花零落》兩種。從他的創作歷程而論,以司馬翎為名的一段時日,是成果最輝煌、收穫最豐碩的黃金時期。早期名家,如臥龍生、古龍皆對他贊不絕口,宋今人稱許其為「新派領袖」、張系國讚譽之為「作家中的作家」 ,葉洪生則認為其生前名氣雖遜於二龍(臥龍生及古龍),「實則卻居於『承先啟後』的樞紐地位,影響甚大」 ,在老一輩的讀者群中,司馬翎往往是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以他部部紮實、精采不凡的作品質量而言,理應能讓他的名聲永持不墜才對;然而,除了老讀者而外,他受重視的程度,卻遠遠遜於聞名遐邇的金庸、古龍、梁羽生諸「大師」,除了葉洪生先生對他「情有獨鍾」之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為他推介;從受歡迎、流傳的層面而言,似乎亦不及臥龍生、諸葛青雲、東方玉、柳殘陽等擁有廣大的新舊讀者,在武俠小說出租店中,他總是委委屈屈地踡伏在偏僻的角落。窺其原因,可能有兩點,其一是司馬翎過早中輟寫作生涯,1971年以後,他歸返香港經商,在此時期,由於武俠小說出版界的混亂情勢(主要是著作權法問題),「司馬翎」之名,幾乎成為一切冒名偽作的代名詞,非但如《豔影俠蹤》、《神雕劍侶》等猥濫諸作,假其名以問世,就是金庸的作品,在出版商運作之下,也大量以「司馬翎」的招牌,偽版印出,如《一劍光寒四十州》、《獨孤九劍》(即《笑傲江湖》),《神武門》、《小白龍》(即《鹿鼎記》)等,造成了讀者「司馬翎就是金庸」的錯誤印象,在金庸挾媒體的雄厚力量席捲了臺灣武俠小說界之後,司馬翎的光芒,被掩蓋殆盡,雖然晚期欲有所作為,已是時不我予了。 其次,司馬翎成名期間,臺灣學術界仍然視武俠小說為旁門小道,所有的武俠作品,包括金庸在內,都不能登大雅之堂,自然沒有任何人願為他張目、推介了;而1980年以後,由於金庸旋風的影響,儘管相關的武俠論述,得以大量正式披露,卻在「商品化」的傳銷策略主導下,集矢於金庸一人,論者幾乎「無暇」顧及其他的作家,司馬翎還是無法引人注意。1985年以後,大陸興起一股「武俠小說熱」,學界亦順風駛船,展開以武俠小說為主的通俗小說研究工作。大陸的研究、論述,層面較廣,眼界較雜,在芸芸武俠作家中,司馬翎倒算是一顆較引人矚目的新星,陳墨《新武俠二十家》 ,即以他為「臺灣小說四大家」之一。但是,由於大陸出版界魚目混珠、張冠李戴的情形,較諸臺灣更形混亂,司馬翎的作品中,夾雜著許多偽作,大陸學者眼目迷濛,有如「盲俠」,「聽音辨位」之能既少,自然只是迎風亂舞、嚮壁虛說了。 以陳墨為例,在〈司馬翎作品論〉中所分析的三部作品,《河嶽點將錄》、《黑白旗》分別為易容、紅豆公主所作,唯一的司馬翎作品《金浮圖》,也是他較「媚俗」的一部,這卻導致他評論司馬翎為「二流作家」的定位。 事實上,以他的小說藝術造詣而言,在金庸的流麗高華、古龍的詭奇懸疑、梁羽生的典雅平正之外,他能以樸實厚重的風格,獨樹一幟,在武俠作家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平心而論,司馬翎的際遇與他的武俠作品成就,是有一段相當大的落差的,他宛如一顆蒙塵的明珠,未琢磨的璞玉,亟待有識者的發掘,重新為他作定位。 舒徐沉穩--司馬翎小說的特殊的節奏 司馬翎的作品無法像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一般,獲得廣大讀者的歡迎,甚至也不容易獲致學界的青睞,主要的問題,是來自他的作品整體所呈現的質樸厚重風格。 從通俗文學的角度而言,作品「節奏」的掌握,為其是否能真正「通俗」的最大關鍵。結構主義學者傑聶(Gerard Genette)曾經將作品中的事件延續時間與敷衍時間(敘述時間)的比率關係,稱為「步速」(pace),事件延續時間的久暫與文章長短(字數、頁數)的反比越大,則「步速」越快(亦即,事件時間長,文章短) ,此一「步速」,實際上決定了作品情節推展速度的快慢(此處我以「節奏」名之)。 節奏的快慢遲速,原無一定的標準,更不能據以評斷一部作品的優劣,但就通俗小說而言,卻是最重要的指標,這與通俗小說的讀者心理、閱讀傾向是無法分開的。從「通於俗」的角度而言,「俗」是通俗小說的讀者群匯聚之處,由於讀者群的變化,「俗」的內涵也隨之而變,通俗小說較之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具有更大的「隨時以宛轉」的特性,它必須充分掌握「俗」的變化,提供滿足「俗」的一應需要,才能確保其生存的命脈。從作品與文學的關係而論,通俗小說是最能掌握時代脈動的作品,儘管此一掌握的表現方式訴諸於單純滿足需求的形式,而不作縱深式的挖掘,缺乏內省和批判,但是,卻直截而有效地觸及到當代讀者生活層面中所最感到欠缺的質素,而能迅速攫掠到讀者的喜愛。當然,這也無形地注定了通俗小說生命短暫的宿命,尤其是在社會變動迅速的時候,由於生活層面的改變劇烈,同一吸引讀者矚目的質素,勢必無法持續,就難免成為過眼雲煙了。 社會生活層面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生活節奏的急遽速化,讀者本身的生活節奏,在閱讀作品時,往往會和小說中的節奏自動作湊泊或調整,這種調整大部分是由讀者主觀意願主導的,讀者可以放緩、持續甚或加速自身的節奏,以取得和作品節奏的協調。此一主觀意願,往往與讀者的閱讀目的有關,以嚴肅、求知心態閱讀的讀者,通常會放緩自己的節奏,以細膩的眼光,蒐尋任何從字裡行間所可能流溢出的訊息,予以反思;而以閒情逸致或急於獲得迅速滿足的心理閱讀作品,則大體上不是延續即是加速原有的生活節奏。通俗小說的娛樂休閒傾向,原就為滿足一般讀者生活上的所需而產生,因此,通俗小說的節奏必須與讀者的生活節奏取得默契,才能獲得歡迎。以三0年代的武俠小說為例,還珠樓主、王度盧等作家的作品,在早期臺灣武俠小說的讀者群中,還具有吸引力,這不但是一些「老讀者」津津樂道的盛事(葉洪生的《蜀山劍俠評傳》可視為代表),就是臺灣早期的武俠作者,如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也不諱言曾取徑於這些先輩作家,初期作品清一色的「舊派」。六0年代的讀者,由於社會的進步,生活節奏明顯加速,讀者已不易「欣賞」「慢工出細活」式的冗長敘事筆調,先輩作家已開始了步上寂寞的路徑。連帶著,後進作家也不得不作調整與更張。古龍在所有作家當中,對節奏最為敏銳,六0年代末期,《多情劍客無情劍》以變幻不羈的筆法,闖開了「古龍世紀」,影響所及,至今披靡。七0年以來,王度盧、還珠等先輩作品陸續翻印出來,所受到冷落,可以以「悽慘」一言蔽之,擺在租書店中,幾乎沒有人問津。原因何在?三0年代的敘事節奏,已明顯無法配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這是無庸置疑的。 武俠小說向有所謂「新派」 之說,事實上,「新派」的崛起,正是緣於情節節奏由慢而快的轉變,司馬翎小說的創作巔峰時期,正處於新舊世代交替的時候,而整個敘事的筆調,在節奏上相較於先輩作家已有明顯的增進,這點,從早期《劍神傳》系列與中期自《聖劍飛霜》而下的作品比對中,可以窺探得出。宋今人曾謂司馬翎對「新派」,「有創造之功」,並許其為「新派領袖」 ,若從「開風氣之先」的角度而言,是很確切的看法。不過,司馬翎的「新」,卻與古龍等人的「新」不同,是屬於有節制性的「新」,既能避免先輩作家冗長的景物描述及成段成篇的插敘、補敘,使整個節奏進展如水流不竭,涓涓而溢;又不至於破碎斷裂,如拆七寶樓臺,不成片段 ,反而成為他獨特的風格。至於後期的《強人》、《極限》諸作,司馬翎取法古龍,以變化快速的場景鋪敘情節,反倒失其故步,令人不無遺憾。 事實上,司馬翎的特長在於舒徐沉穩、從容不迫,這是他的小說迥異流俗的展現,在六0、七0年代,臺灣社會的生活節奏是與他的風格合拍的,以此,攫掠了許多老讀者的喜愛。不過,這也是他「蒙塵」的主因之一,越接近現代的讀者,生活節奏越快,已較無法接受舒徐沉穩的敘述方式,「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不得不從他所擅長的「推理」說起。 縝密推理--司馬翎的絕活 宋今人認為司馬翎的作品,「有心理上變化的描寫,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闡釋,有各種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啟發」 ,很能抉剔出司馬翎節奏的特色。 「推理」是司馬翎小說獨具一格的,但並不是日本式的「推理小說」,因為司馬翎儘管也非常注意情節的撲朔迷離、跌宕多變,但卻未採用「破解謎團」的懸疑布局(唯一可以說含有濃厚「推理小說」意味的,是《杜劍娘》一書),反而藉人物內在心理的變化,以智慧與理性對各種事物、觀念作深刻的分析。「理性」的思維,是司馬翎小說中所有人物共通的特徵,上自主角,下迄若干不起眼的配角,司馬翎皆刻意營造其理性的思維。以《丹鳳針》22集中的一個不起眼角色尤一峰為例,他是個「眉宇之間,則透出一股慓悍迫人的神情」(頁15)之人,通常這類人的特色是勇而無謀,以粗暴取勝,可是司馬翎卻著意寫其細膩的思致,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處理他與凌九重之間彼此勾心鬥角的場面。連如此一個人司馬翎皆賦予他如此縝密的思維,以此可概其餘。 為表現出理性的思維,司馬翎不得不將重心置放於人物的心理分析與情節的「推理結構」中,以此也無形中使他的情節節奏放緩許多,以《檀車俠影》中一場「救人」的情節為例,從林秋波開始發現到敵蹤,歷經中伏、受困、解穴、克敵,到最後林秋波飄然遠去,事件時間不過短短幾個時辰,作者卻以將近兩本半的篇幅(約150頁)詳加描摹,其間欲救人反遭擒的林秋波,心緒可以說是瞬息萬變,而受援的秦三錯、挾持人質的幽冥洞府三高手(尉遲旭、黎平、黃紅)亦是幾度深思熟慮,彼此機鋒互逞、鬥角鉤心,寫得相當淋漓盡致。但是,就全書的結構而言,此一大段落的作用,僅僅在於凸顯林秋波、秦三錯這兩個次要角色的性格而已(林秋波交雜於修道及動情的心緒、秦三錯邪惡而具有人性的性格)。習慣於情節迅快進展的讀者,於此可能會感到不耐煩,但是閱讀時喜歡思考的讀者,卻會興致盎然、拍案稱絕。然而,武俠小說的讀者,多半是以情節為主的,這使得司馬翎的愛好者往往限於文學程度較高的群眾,因而影響到他的普遍流傳,畢竟,宋今人所稱許的「深度、含蓄與啟發」,是屬於較高層次的閱讀。 「推理結構」在司馬翎小說中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當屬其中的「鬥智」場面。在他的小說中,闖蕩江湖的豪士並不截然以「武功」為最大的優勢,反而處處凸顯「智慧」的關鍵力量,甚至可以說「智慧」才是唯一的憑藉,逐鹿江湖,「智慧」隨時可能產生轉敗為勝的作用。在《劍海鷹揚》中,司馬翎藉典型的智慧人物端木芙,引發出一段足以代表其風格的文字: 眾人這時方始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這個道理,在以往也許無人 相信。尤其他們皆是練武之人,豈肯承認「智慧」比「武功」還厲害可 怕?然而端木芙的異軍突起,以一個不懂武功、荏弱嬌軀,居然能崛起 江湖,成為一大力量之首。以前在淮陰中西大會上,露過鋒芒,教人親 眼見到智慧的力量,是以現下無人不信了。 因此,在司馬翎的筆下,所有的人物,包括了若干實際上無足輕重的角色,都具有縝密的心思、冷靜的頭腦,絕非一般小說中一味粗豪的可比。在《獨行劍》一書中,司馬翎更設計出一個「智慧門」,以「智慧國師」領銜,將整個江湖世界的角鬥,從武力的戰場,移轉到智慧的競爭,其間無論是正派人物的朱濤、陳仰白、戒刀頭陀,或邪派的秘寨領袖俞百乾、智慧門諸先生,在武功上儘管各有所長,但真正克敵致勝的關鍵,卻在於智慧的運用。 在此之下,司馬翎實際上已「顛覆」了「舊派」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改變了江湖的體質。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本是個「尚武」的世界,誠如司馬翎所說的,「這是一個崇尚武力的世界,你越有氣力,和武藝越精的話,就越受人尊敬」 ,武功,非但是英雄俠女行走江湖的憑藉(護身)、仗義行俠的條件(行俠),更是解決紛擾、快意恩仇的最終法則;事實上,武俠小說之以「武」為名,正緣於有此「武功」撐起整體架構。因此,「武功排行榜」隱然成為武俠小說中的慣例,一如古典說部中的《隋唐演義》,排名在後的一定爭不過排名在前的,宇文成都排名為「第二條好漢」,其他「好漢」註定無法勝他,他也註定要在「第一條好漢」李元霸下吃癟受虧;而「第一條好漢」無人能勝,只得安排他受雷殛而死。慕容美的《公侯將相錄》,依公、侯、伯、子、男的位階,排定江湖次序,是最典型的例子。武俠小說中必須安排「武林秘笈」的情節模式,以打破這個規律,亦是不得不然。古龍後期的武俠小說不取「秘笈」模式,可謂一大改變。此一改變,古龍的「兵器譜」(《多情劍客無情劍》)開創的是一個「當下情境」的局面,天機老人、龍鳳雙環、小李飛刀……等,雖以武功高低為序列,但爭勝的關鍵,卻在於面臨決勝時的一些細微變化,如地形、地勢、體力、心理狀態等的影響,隨時可以扭轉高低序列,楚留香之能夠擊敗武功遠高過他的石觀音、水母陰姬(《楚留香傳奇》),正緣於此。古龍的手法,明顯取法於現代運動的競賽,所謂「球是圓的」,勝負很難預作定論,熟悉運動此一「非法之法」的讀者,應該頗能感受到古龍此類安排的合理性。司馬翎開創的則是另一格局,在逞強鬥勇、劍影刀光江湖中,凸顯出理性的決定力,這不但使他所構設的江湖世界是「鬥力又鬥智」的場合,更以此發揮了他自己所擅長的「雜學」,隨時藉智慧的表徵,如奇門遁甲、陰陽術數、佛學道思、醫學藥理等,刻意點出。 精通百家--司馬翎的「雜學」 武俠小說是一種包容性甚廣的類型小說,在江湖的背景下,可以寫俠客的豪情、英雄爭勝的酣暢淋漓;可以寫兒女情長、刻骨銘心的愛恨情仇;也可以寫歷史宮闈、複雜多變的權力徵逐;更可以寫懸疑緊張、科技幻想的情節,而「雜學」,正是支撐這種豐富內涵的砥柱。 「雜學」運用於小說創作,唯有武俠小說才能發揮其效用,蓋武俠小說本身就是中國文學中極為特殊的一種體裁;而整個背景,也以舊時代(清以前)為範圍,因此傳統文化的適時添入,無形中即加強了整個小說濃厚的中國風味。武俠小說在海外華人地區風行一時,甚至成為「華僑子女的中文課本」 ,事實上就是以這傳統的文化氣息吸引讀者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向來以學識淵博著稱,「書卷氣」甚濃,無論琴棋書畫、茶酒花食,藉書中情節隨時點染,將傳統文化知識濃縮於小說之中,享有傳統文化「小百科全書」的盛譽 ,這在今人已逐漸淡漠於傳統文化的趨勢下,反而可以因閱讀武俠小說,而隨處「驚豔」,獲得智性的領略,也成為武俠小說立定根基的命脈了。 司馬翎「雜學」的豐富,在武俠小說家中是很特殊的,舉凡佛學道家、陰陽五行、勘輿命理、陣法圖冊、土木建築、醫學藥理、東瀛忍術,甚至神秘術數,信手拈來,說得頭頭是道,無不令人驚喜。例如《掛劍懸情記》中花玉眉的「陣法之學」,隨手幾根樹枝,便可以導致眼目迷濛、視域混淆的效果;《丹鳳針》中雲散花的「忍術」,以隨身披風掩蓋,就可以「木石潛蹤」(藉自然物隱蔽形藏);《情俠蕩寇誌》中幾場官軍與海盜的海戰,脫胎於兵法,寫得寫得氣勢宏偉、驚心動魄;《飛羽天關》中李百靈的勘輿之術,經由作者引經據典予以闡發,更令人嘆為觀止。在此,司馬翎靈活運用中國傳統的「雜家百技」,使得小說中處洋溢著傳統文化的氣息,雖然不無故神其技的用意,卻能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在武俠小說家中,司馬翎的「雜學」,是足以與金庸並立而無愧的 。不過,金庸雜學的優長為文化與歷史,而司馬翎則於哲理、術數別有獨見,迥非一般作家可比。尤其是在有關傳統的奇門秘術方面,用力之勤,見解之精到,居然有專門名家的氣勢。武俠小說利用傳統道教術數刻畫武學,是普遍的現象,但大底皆以淡筆帶過,以金庸之能,在《神雕俠侶》中寫黃藥師所排的「二十八宿大陣」,儘管名目繁多,不過只能將五行、五方、五色、二十八宿相應的道理,簡要敘述,實際上並未能說出其所以然來;司馬翎則不然,在《飛羽天關》一書,司馬翎將堪輿、陣圖之說化於小說情節中,神奇詭妙,而又引據確鑿,相較之下,顯又略勝一籌。 當然,這裡不免牽涉到傳統雜學(尤其是術數)的可信度問題,例如「陣法之學」,究竟實情如何,不免讓人匪夷所思。不過,從小說「虛構」的角度而言,即使司馬翎完全嚮壁虛說,也不妨礙讀者領略箇中趣味,甚至可能因為他敘述手法上的「理性分析」,而引領讀者對此問題作更深入的思索,從而產生濃厚的興趣。事實上,傳統的文化內涵,未必沒有其道理,否則也不可衍傳千百年之久,更何況,有些道理,是的確可以獲得科學驗證的。李嗣涔曾作過一個有關「魔音穿腦」的實驗,證實了武俠小說中以「聲音」當武器的可能性,對司馬翎小說中「心靈修練」、「氣機感應」等的武功描述,從「人體科學」的角度,予以認可,推崇其「意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以此可知司馬翎絕非純粹「虛構」,而是真有豐富的雜學知識支撐的。當然,司馬翎的雜學也包含了現代的知識,在《掛劍懸情記》第3集中,司馬翎設計了一個「心靈考驗」的情節,擬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觸「精神催眠」對人類意志力的影響 ,從書中人物的反覆辨難、絲絲入扣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見作者於此學的功力。 司馬翎的「雜學」,在他的小說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在此,我們可以從他對「武功」別出新裁的設計,以及書中隨處透顯出的「道德關懷」予以探討。 司馬翎的武功設計與道德關懷 武俠小說以「武俠」為名,自然必須展現出俠客的武功。中國的武術,自有其淵遠流長的傳統,而從俠義小說到武俠小說,武功的設計,自始也是重要的一環。古典俠義小說中,唐代以神秘性濃厚的道術取勝;宋元以來,則棍棒拳腳,步步踏實;明清之間,此二系相互援引,分別有所開展,既有平穩紮實如《綠牡丹》、《兒女英雄傳》的,也有光怪陸離如《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的,基本上,初步奠定了民國武俠小說的兩大武功設計系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則分別標識了兩大系的開展。不過,神怪一系,自還珠樓主《蜀山系列》以降,甚少創發;而平實一系,則自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後,逐步擺脫以純粹中國武術描述武學的窠臼,走上「武藝文學化」的「虛擬武學」。所謂「武藝文學化」,是指作者設計的武功,只能藉文字領略其妙境,而未必能於現實施展,而且,通常以優美的文字引首,為其武學命名。就武俠小說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不僅作者可以超越個人體能限制,依其深厚的學養,憑藉文學想像,設計各種冠冕堂皇、名目儼然的武功,讀者也可在這些變化莫測,而又似乎言之成理的武功中,沉浸於想像的武林世界中。這些武功的摹寫,道教養生術中脫胎而出的「內功」(通常以武當派為代表,但運用之廣,則可遍及所有武俠人物),是為主流;但變化之妙,存乎一心。在武俠名家中,金庸著名的「降龍十八掌」、「黯然銷魂掌」、「獨孤九劍」,首先在「虛擬武學」上廣獲佳評,大抵皆利用詞語串連,「顧名思義」,如「降龍十八掌」第一招「亢龍有悔」,據金庸所描述: 這一招叫作「亢龍有悔」,掌法的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 倘若只求剛猛狠辣,亢奮凌厲,只要有幾百斤蠻力,誰都會使了。……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因此有發必須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 留在自身的力道卻還有二十分。那一天你領會到了這「悔」的味道, 這一招就算是學會了三成。好比陳年美酒,上口不辣,後勁卻是醇厚 無比,那便在於這個「悔」字。 很明顯地,這段文字以「亢」字所代表的「充盈」義和「悔」字的「潛藏」義對舉中,創發出來,頗符合道家「持盈保泰」的理論 ,可謂別開生面。60年代後的古龍,則創發出「無招勝有招」之說,完全屏除了招式名目,簡截了當,開創了新一代的武功描寫典範。不過,在武功本身著墨不多,算是異峰突起的「別派」。司馬翎的開創性雖不如金、古二人,但介於兩家之間,卻自有其特色。司馬翎論武功以「氣勢」取勝,所謂的「氣勢」,實際上是一種心靈的力量,根源於道德與理性,不僅僅是人天生的性格與稟賦而已,在《血羽檄》中,司馬翎藉「白日刺客」高青雲面對「鳳陽神鉤門」的裴夫人時的一段解說,和盤托出他設計此一武功的底蘊: 古往今來,捨生取義的忠臣烈士,為數甚多,並非個個都有楚霸王的剛 猛氣概的,而且說到威武不能屈的聖賢明哲之士,反而絕大多數是謙謙 君子,性情溫厚。由此可以見得這「氣勢」之為物,是一種修養工夫, 與天性的剛柔,沒有關係。 在此,司馬翎所援用的觀念,來自於傳統儒家,故其下又引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為佐證。蓋高青雲雖為受賂殺人的刺客,卻與一般刺客不同,正義凜然,善惡分明,而裴夫人一則有愧於丈夫,二則被懷疑為殺死查母的兇手,於道德有所虧欠,因此,高青雲仗此道德的正義力量,足將其「氣勢」發揮到淋漓盡致,使得原來尚可力拼的裴夫人,一時無法抵禦。當然,此一「氣勢」也並非決定格鬥勝負的唯一標準,同時,也不是完全無可抵禦的。司馬翎將「氣勢」歸之於道德理性,則另一種非關理性,純粹出之於強烈情感衝動的愛情力量,亦足以與之抗衡。因此,當裴夫人思忖及他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查思雲復仇,無愧於心時,又足以在鬥志崩潰的情勢下,陡生力量,使高青雲恍悟到「原來真理與理性,唯有一個『情』字,可以與之抗衡,並非是全無敵手的」 。在此,司馬翎顯示了他對人類心靈力量的洞識。 此一對人類心靈的洞識,使司馬翎在武功設計上常有令人激賞的表現,以「情」字而論,金庸在《神雕俠侶》中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別賦〉)的文藝化方式,設計出膾炙人口的「黯然銷魂掌」,意欲強調「相思」的偉大力量,唯有「哀痛欲絕」之時,才能發揮其莫大的效力,可謂是神來之筆,將武學文藝化的精微發露極致。讀者心領神會之餘,也許不免忽略了,當楊過在「心下萬念俱灰,沒精打采的揮袖捲出」 時,何處激生情感的澎湃動力?相對之下,司馬翎在《白刃紅妝》書中,設計了斷腸府的「情功」--據書中所述,斷腸府「情功」修鍊之要訣在於藉情感的力量以增強武功,府中弟子必須以各種方式激起對方的「真情」,對方情感投注愈深,自己獲利也愈大;反之,一旦自己陷溺不返,動了「真情」,亦將因之而削弱武功,甚至情絲牽纏,氣息奄奄--無論是對情感的力量與人面對情感時的不由自主,都有相當深刻的描繪,蹊徑別出,卻又合情合理。 司馬翎武功的設計,不僅在別出新裁地呈顯書中人物五花八門,令人目眴神移的武功而已,事實上,就在武學設計中,也顯示了其道德的關懷。前面所述的「情功」,原是邪派斷腸府的絕技,必要使對手心碎腸斷而後已,可是,當書中邪派的角色(曹菁菁、王妙君、程雲松)一旦面對自己的「真情」時,卻是寧可受「情功」反噬之苦,九死不悔,其中逼出了作者對人類至情至性的肯定。 在武學方面,司馬翎心目中時時有一「武道」的觀念,並用此名,創作了《武道‧胭脂劫》 一書,正可代表司馬翎對人類生命道德的關懷。 從江湖世界憑藉著武功裁斷是非的角度而言,武功的極境,事實上就是權力的極境,這點,多數的武俠小說都已展示了相當一致的共識。因此,武俠小說的結局,通常免不了出現一場武功/權力的對決,以決定江湖勢力的消長。不過,這種對決的形式卻又相當弔詭,作為權力象徵的武功,最終的目的卻是在「顛覆」權力。「以權力反權力」,未免有「以暴易暴」的矛盾,卻和武俠小說「止戈為武」的性質是相合的,這是武俠小說最具辨證性的地方。「以權力反權力」之所以能成立,在於前者的外在形式(武功)被賦予了道德的內涵(善),而後者則是違反道德的(惡);同時,後者的權力性質,是一種集權性的強橫統治,而前者則出於一種權力平衡的概念--權力一旦是平衡的,即無權力可言,是故武俠小說中如果有最後的「武林盟主」誕生,也必然是「無為而治」型的,甚至,更多的武俠小說以「退隱山林」的方式,迴避了權力集中的可能。以此而論,武俠小說的基本精神是反權力的。 權力是現實社會中無法否認的存在,虛構的江湖世界既以人世為藍本,自也無法不涉及權力的徵逐。人在現實社會中,可以自外於權力角逐,默默無聞;然而,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既以「武功」(權力的外在形式)為主體,就無法自外於此,是則,個人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安頓,該與權力如何應對?這是武俠小說必須處理的問題。可惜,多數的武俠小說都輕易放過了這原可以極力發揮的主題。相對之下,司馬翎的《武道‧胭脂劫》正在這一方面提供了若干深刻的觀點,足以發人省思。 《武道‧胭脂劫》以「武道」的探索為主線,先從霜刀無情厲斜追尋魔刀的最後一招為始點,深刻切中了「武功」與「權力」的關竅。厲斜畢生以「武道」的探索為終極,不惜以殺生歷練的方式,揣摹魔刀至高無上的終極心法;然而,此一「武道」的最終意義,不過是能使他成為天下武功最高的人,擁有旁人不敢冒犯的權力而已--武功就是權力的事實,在厲斜身上表露無遺。假如我們將厲斜一連串磨練探索的過程,視為他個人生命意義的發掘過程的話,毫無疑問地,厲斜企圖將生命安頓於權力的競逐上。 沈宇的出現,是厲斜生命史上重要的一個轉折。沈宇身負沉冤,以自苦為極,對人生原已無望,然而在目睹厲斜以人命為試練的慘酷手段下,雄心頓生,意欲憑藉個人的智慧才幹,防阻厲斜為禍。沈宇並未視厲斜為惡人,相反地,他認為厲斜不過是欲探索「武道」的奧秘。問題在於,沈宇以悲天憫人的胸懷思索「武道」的極致,徑路與厲斜完全異轍。「武道」的究竟何在?權力能否安頓生命?司馬翎在此書中,利用了許多精采的情節,舒徐沉穩地鋪敘而出。最後,厲斜終於發現了魔刀最後一招的奧秘,原來,那是一把刀,當厲斜最後手執這把不屬於他追尋的意義內的「身外之物」時,頓時覺得大失所望,對他而言,這是多大的反諷呀!武功的奧秘,或者說權力的奧秘,竟然就是一把刀,厲斜可能將生命安頓在這把刀上嗎?厲斜終究不能不以退隱的方式,棄絕此一權力。 在此書中,作者刻意安排了一個「假厲斜」,藉對比凸顯武功與權力的關係。假厲斜是謝夫人的「身外化身」,而謝夫人雖然出場次數不多,地位卻非常重要。她原來是以「性」為人生極樂的淫娃蕩婦,在偶然的機緣中,嘗到了血腥的快感,從此將對「性」的追求,轉化成對暴力、血腥、殺戮的畸型欲求,因此以「身外化身」製造了假厲斜,在江湖中展開無情而狠毒的殺戮。性與暴力血腥,和權力一樣,都是潛藏於人內心的原始衝動,就權力的本質而言,事實上正操控著性與暴力,因此,謝夫人實際上是厲斜的一個「身外化身」。這種瘋狂的原始欲望,最後導致了謝夫人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獨子謝辰和兒媳胡玉真,實際上也暗示了權力徵逐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泯滅人性的。謝夫人最後被厲斜一刀斬絕,厲斜於此時才算真的體認到權力的可怕,從而能真正的擺脫受權力欲望操控的生命。 謝夫人的角色,是武俠小說中相當特殊的設計,然而,司馬翎並無意去批判這位既淫蕩而又慘酷的女性,相反地,我們透過他對謝夫人深入的心理摹寫,可以發現,謝夫人不過是一個象徵--一個集性與暴力的權利追逐者的象徵,這是「胭脂劫」書名的意義。司馬翎與所有的武俠作家一樣,秉持著武俠小說「反權」的基本精神,同時,更在「反權」中,展示了他的道德關懷。 沈宇含冤莫白的際遇,一度使他灰心喪志,儘管後來他赫然發現沉冤可雪,也因此獲得了愛人艾琳(艾琳是他青梅竹馬的情人,誤以為沈宇之父為其毀家兇手,因此千里追蹤,內心糾纏於親仇與情愛的矛盾中,寫來也非常出色)的諒解,但是,真正激發他雄心壯志的,卻是一股正義的道德力量。也正因他自道德重新燃起生命的意志,才能昭雪沉冤!從沈宇身上,司馬翎的道德關懷,已經是非常明顯了,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陳春喜這角色的設計。 陳春喜原來是漁村中的小姑娘,單純而直樸,卻嚮往著江湖中叱吒風雲的生命形態,在胡玉真引介下,她投入了謝家這個謝夫人的權力核心,透過謝辰,修習「蘭心玉簡」的武功。「蘭心玉簡」是謝辰為他的母親謝夫人千方百計尋求,欲使謝夫人變化氣質的武學,可是權力象徵的謝夫人不願修習,因為這武功與權力欲望衝突,「這種心法以純潔無邪為根,以慈悲仁愛為表」 ,修習過後,「這顆心真是空透玲瓏,纖塵不染,已經少有心情波動的情形了」 。權力等同於欲望,而「空透玲瓏,纖塵不染」,自然與權力絕緣,陳春喜以純真之心地,投身於權力中心,事實上是司馬翎所安排的見證--透過自始至終未變化的純真,見證權力之可怖與道德情操之高尚。 魔刀的最後一招,關鍵居然是把刀;權力徵逐的下場為何?謝夫人身首異處,厲邪恍然了悟。「武道」的奧秘何在?司馬翎意欲告訴我們,「道在人,不在物」,在人高貴的道德情懷,在人的慈悲與仁愛,這是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人與武功合一的終極境界,平實簡捷,意義卻深刻警策,事實上,這才是真正的「武俠」! 自足生命的開展--司馬翎筆下的女性 在武俠小說「俠骨」與「柔情」兼備的風格中,女性俠客無疑已成為武俠小說描繪的重心之一。小說中的「江湖」儘管可以脫離現實,任情「虛構」,簡化了現實中林林總總的複雜面相(如正義與邪惡的道德規律、殺人流血的法律規範等),但是,「人物」卻是「模擬」現實情境的;社會上有形形色色的女性,小說中自也應有各具丰采的女俠,我們可以看到,武俠小說中的女性,從空門中的尼姑、道姑,到千金閨閣、江湖名家之女、神秘幫會的首腦,乃至於三姑六婆、妓女貧婦,應有盡有;至於在形貌、性格上,俊醜兼具,內涵複雜,更是不在話下,其實也與現實社會(小說中古代的現實社會)可能出現的女性範疇相當了。從這點來說,女性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正如其他類型的小說一樣。 從武俠小說發展的歷史而言,女性俠客的出現,整個影響到江湖結構上的體質改變,主要的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這不但使得江湖的陽剛氣息得以藉「柔情」調劑,更連帶影響及英雄俠客的形貌與性格的描繪 ,關於這點,陳平原曾分析: 首先,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武功第一,而是人 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其次,男女俠客都不把對方僅僅 看成打鬥的幫手,而是情感的依託……,也就是說,不是在剛猛的打鬥 場面中插入纏綿的情感片段來「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作為常人必 然具備的七情六欲,借表現其兒女情來透視其內心世界,使得小說中的 俠客形象更為豐滿。 大抵自王度盧的《鶴驚崑崙》五部曲後,武俠小說中的「柔情」,已經成為此一文學類型中不可或缺的成素了,而主要承擔起這個任務的,無疑是女性--尤其是女主角。在此,武俠小說頗有幾分「才子佳人」的味道,不但兀傲英雄與巾幗紅粉,總是刻意安排得相得益彰,而且情感描摹也往往可以細膩入微,令人蕩氣迴腸。 不過,在芸芸江湖世界中,究竟女性可以作如何的設計?基本上,一般武俠小說中所刻劃的女性,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柔弱可憐型的,性格溫柔、情感細膩,一副「亟待拯救」的楚楚情狀,是英雄俠客展現生命華彩的憑藉,仗義行俠的英雄,最樂於藉援救的過程凸顯出過人的英風豪氣,如金庸《神雕俠侶》中的程英、陸無雙。第二種是「魔女淫娃」型的,通常被描摹成因感情失利,由愛深恨,轉而向全天下的男人進行「肉慾式的報復」;或者甚至天生就是「性饑渴」,眼底下見不得男人,最擅長的就是「以色迷人」。她們是英雄磨練人格和品性的對佳對象,對這種美人,英雄不但往往可以輕騎過關,而且還可以藉斬除剷滅的行為,建立英雄的聲譽或品牌,如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林仙兒。第三種是「俠女柔情」型的,可以溫婉體貼,可以機伶多智,可以武藝高強,可以天真無邪,不過都必須對英雄一往情深,無怨無悔。她們是英雄仗劍江湖並轡而行的佳侶,是英雄心心繫戀的紅粉知己,只有她捫才能在英雄鐵血的心湖中激蕩出陣陣波濤。她們最主要的作用,可能是當一面鏡子,在英雄意氣風發之餘,迴首觀照,會發現自己和凡人一般,也是需要愛情滋潤,可以談戀愛的!如金庸《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這三類彼此間交揉重疊,大體上是可以涵蓋一般武俠小說形形色色的主要女性的,很少有作家可以超脫於此。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如此的設計,顯然是以「男人心目中的女性」為藍圖的,女性俠客儘管在武俠小說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基本上仍然是以「附庸」的形態出現,女俠自身生命的開展,向來缺乏應有的關注。大體上,能賦予女俠生命姿采,跳脫開男性沙文圈子的武俠小說作家,只有司馬翎!在他筆下的女俠,開展出迥異於一般武俠小說的另一種生命世界! 在司馬翎的小說中,女性往往呈顯出各種不同的風貌,儘管在造型上難免也與其他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雷同,可是無論是對女性內在情感與生命的刻劃,或所賦予女性的尊重與肯定上,都遠較他人來得深刻與細膩。尤其難得的是,司馬翎的筆觸,更拓展及於許多武俠小說從未開展過的女性。 司馬翎筆下的女俠,類型相當複雜,涵蓋層面亦廣,其中不乏若干刻劃深入、綻現出動人姿采、難得一見的特殊女俠,如《劍海鷹揚》中一心向「劍道」探索究竟的秦霜波、智慧高絕,隱然可與男性分庭抗禮的端木芙;《武道‧胭脂劫》中擺蕩於性欲與權力中的謝夫人;《纖手御龍》中精練聰穎的薛飛光、《掛劍懸情記》中嫵媚多智的花玉眉、《金浮圖》中機智溫柔的紀香瓊;《丹鳳針》中開放而自主性極高的雲散花;均能別出蹊徑,刻劃出別具姿采的江湖女俠。 司馬翎總是不吝於讓他書中的女性展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而且,對她們的內心世界均作深刻而細膩的描摹,絕非一般的「扁平人物」可比,而且面貌個性,均各如其分。如《聖劍飛霜》中日月星三公的女兒,絳衣仙子舒倩爽朗亮麗,如陽光耀眼;銀衣仙子佟秀深沉陰柔,如月光朦朧;玄衣仙子冷清影清雅冷漠,語若流星:無不宛肖其人。即使是同樣寫智慧過人的女俠,而薛飛光之精練、花玉眉嫵媚、紀香瓊之溫柔,也莫不各有千秋;其他如《劍神傳》中刁鑽慧黠的朱玲、《纖手御龍》中溫婉柔弱的雲秋心、《鐵柱雲旗》中伶俐天真的單雲仙、《玉勾斜》中冰冷無情的冷于秋、《飲馬黃河》中精明剔透的春夢小姐、《武道‧胭脂劫》中高潔純真的陳若嵐……,隨書翻閱,無不處處令人驚豔。難得的是,司馬翎筆下的女性,固然各具姿態,而作者所賦予的關注,更是遠遠超過其他的武俠作家,如《武道‧胭脂劫》中,「禍水」類型的謝夫人,儘管讓讀者毛骨聳然,但是,司馬翎也未嘗純粹以反面摹寫,反而對她整個從世家夫人轉變成武林禍亂的心路歷程,有詳盡的刻劃。 女俠的自主情感 武俠小說儘管以「俠骨柔情」為主體,不過,江湖畢竟還是權力鬥爭的場合,女性的柔情固然可以繫挽住英雄的情思,卻阻止不了英雄開創事業的雄心與壯志。武俠小說中的男俠或許也會款款深情,夢魂牽縈,可是在他們的生命天秤上,感情畢竟仍只是一種點綴,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李尋歡,的確是「多情」的,可是「多情」的對象是死生義氣的朋友,而不是一心繫念、痛苦煎熬的林詩音,所以寧可「犧牲」自己的情感,成全龍嘯雲;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固然心心戀戀於小師妹岳靈珊,可江湖責任在身,他也只有拋開情愁,勉力投入拯救武林的大業中。兒女情長,原不見得會使英雄氣短,其間妥為安排,更可以使英雄美人平添佳話;然而一旦有所衝突,則無論情感若何,恐皆在割捨之列--畢竟,英雄除了情感之外,仍別有安身立命的所在。女性則不同,固然我們可以看見小說中令人激賞的許多女俠,如金庸《射雕英雄傳》中機智敏慧的黃蓉、《神雕俠侶》中溫柔多情的小龍女、《倚天屠龍記》中慧黠精明的趙敏,但是這些機智、溫柔、慧黠的作用,卻多半是為了她們心目中的英雄而發。女俠一旦情感傾注,則一往無悔,一切的考量,皆以英雄為重心;而一旦情天生變,恨海興波,則為情為愛,可以怨讟可以瘋狂,完全失去理智,《神雕俠侶》中反覆感嘆「情為何物」的李莫愁、《天龍八部》中挾恨報復的甘寶寶、秦紅綿、刀白鳳,都是很好的例子。大體而論,武俠小說中的女性,「有愛則生,無愛則死」,藉愛情滋潤以綻現其生命華彩,也因愛情失落而人生褪色--這是武俠世界中的女性宿命,很少有作者可以超脫。很顯然地,如此以愛情為女性生命中唯一重心(意義)的人物刻劃,是相當具有大男人沙文色調的,在此,女性自身的生命未能獲得開展,充其量不過是點綴英雄的瓶花而已。 司馬翎筆下的女俠依舊擁有細膩的情感,也同樣會心儀俠客的風采,但是在整個情感面的鋪敘中,卻能擺脫一往情深、無怨無悔的慣常模式,其中饒有衝突與掙扎,而此一激烈的天人交戰,決定因素則不僅僅是情感深淺的問題而已,司馬翎通常會安排幾個各具丰姿、特色的正反派英雄,介入女俠的情感生命中,導致女俠面臨徬徨與抉擇的窘境,引發其「自主」的機能,她們必須深思熟慮,權衡情感與其他問題(如善惡、利弊、志趣、個人與社會等)間的比重。如《掛劍懸情記》中的花玉眉,同時有桓宇、方麟、薩哥王子、廉沖四人,足以引起她情感的蕩漾,她必須在這四人當中,細細剖分其優劣,以定歸宿。於是,各男俠的獨特風采,獲得了盡情表現的機會。桓宇的正直憂鬱、方麟的孤傲脫俗、薩哥的機智多情、廉沖的陰險詭詐,無不淋漓盡致。桓宇最後的脫穎而出,雖是早就可以看出,但是其間各種情境的變化,卻隨時可能導致逆轉,讀者猶不免提心弔膽。在此,花玉眉的生命層次隨著故事情節的延續,屢有成長與拓展,決非僅僅陷溺於情感的漩渦中而已。《劍神傳》中的朱玲,夾雜在正直仁厚的男主角石軒中、貌醜而心細的大師兄西門漸、俊美狂傲的宮天撫、無情而深情的張咸之間,幾度波瀾,幾翻跌宕,如風捲柳絮,難以遽斷歸宿,作者藉一波三折的情節發展,將朱玲的內心情感與心事,描摹得盡致淋漓,而最終的選擇,雖然還是情歸俠客,可是卻因多了這番波瀾,其「自主性」也更凸顯了出來。正緣於此,司馬翎筆下的女俠,以「情感的自主性」獲得了在其他小說中難以企及的豐富深刻的生命層次。 《丹鳳針》中的雲散花是個相當成功的例子,書中以「彩霞多變」 為其性格的寫照,在故事中,雲散花一開始就不是處子之身,但卻非淫娃蕩婦之流,只是較任情任性而已(這已和多數武俠小說牢牢繫念於女主角的貞操不同),因此,既先與性格倔傲、自私自利的凌九重有一吻之情,復又對英挺瀟灑的孫玉麟心生好感;及至她遇到儒雅正直的杜希言後,不但深心仰慕,而且與他有了肌膚之親。依照武俠小說的慣常寫法,雲散花應該死心塌地,心心繫念於杜希言了;可是,雲散花非但因自己已非完璧,「自覺」不配,同時在後來既因察覺到凌九重對她實際上亦真情相待,而與他發生關係;又對外貌溫文的「白骨教」妖人年訓,考慮及婚姻問題;最後則與半路上殺出來的黃秋楓持續發展。每一段情感的波動變化,作者皆細膩委婉地將其心理變化和盤托出,而也不時地給雲散花自省的機會,「我幾乎已變成人人可以夢見的巫山神女,只要我還喜歡的人,就可以投入他的懷中。唉!我現在算什麼呢?」 究竟雲散花將情歸何處,連她自身也不曉得,正呼應了「彩霞變化」的主線,使得雲散花成為書中相當特殊的角色。 司馬翎江湖中的「女智」與「女權」 一般武俠小說慣於將江湖寫成是男性角逐權力的場合,吝於讓女性於江湖中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女性一旦妄圖涉足角逐,通常也是以「禍水」的姿態出現。如《多情劍客無情劍》中以色相牢籠英雄的林仙兒,幾乎集陰險、淫蕩、善變、狠毒於一身,古龍的反筆批判意味甚是明顯。司馬翎則經常以正面的筆法寫女俠,甚至將江湖中扶顛定傾的重責大任,託付於女性身上。花玉眉率領群雄對抗野心勃勃的鐵血大帝竺公錫,淵渟嶽峙,隱然就是中流砥柱,作者將她刻劃成智慧超群、思慮周密的女俠,擔負起挽救武林甚至國家安危的唯一角色,頗能渲染出另一種風格迥異的女俠。這種「智慧型」的女俠,是司馬翎最鍾愛、最樂於刻劃的,因此出現的比率也最頻繁。花玉眉、紀香瓊固然如此,尤其是端木芙,以一個不識武功的女子,憑藉著謀略與陣法之學,不但能在正邪兩大勢力(翠華城主羅廷玉與七殺杖嚴無畏)間縱橫捭闔,巧妙周旋,更結合著矛盾的民族情結,不失立場、尊嚴地聯結疏勒國師的勢力,於江湖中鼎足而三,充分展現了高層次的女性智慧。相較於金庸《天龍八部》中的王語嫣,是更傑出的。 同時,我們更當注意,司馬翎於此還更有拓展,如花玉眉之所以肯如此苦心孤詣,抗衡竺公錫,並不是為了「輔助」桓宇,而是她「關心大局,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百世之功」 ,是個人的志趣!類似的女俠,所在皆有,《金浮圖》中的紀香瓊,以絕頂智慧「選擇」了可正可邪的金明池為其終身伴侶,所展現的除了情感之外,更是自我價值的完成,「她卻感到金明池詭邪險詐的性格,好像有一種強烈無比的魅力。使她覺得如若能夠把他征服,收為裙下之臣,乃是世間最大的樂事」 ;值得重視的是,此一自我完成並不是純粹的好勝爭強之心,而是隱含著濃厚的道德悲憫情懷的。紀香瓊欲透過金明池習練「無敵佛刀」以化解其邪氣,事實上是藉智慧展現出其對人類善性的關懷與認同,「老天爺當知我渡化了此人,該是何等巨大的功德」 。在此,司馬翎賦予了女性其他作家所吝於開展的深廣的生命層次。在他筆下的女俠,情感的比重固然深重,但是被安排成以智慧的、理性的態度去思索她們生命中「應有」(和男性一樣)的意義與價值,這就遠遠超脫了其他武俠小說的牢籠,而展現出不同的江湖世界。《劍海鷹揚》中的秦霜波,是司馬翎特殊設計的一位女俠,她以探索「劍道」的奧秘自期,全書極力鋪揚她在完成此一「自我實現」過程中的種種困頓與波折,尤其是在面對情感與求道間的衝突與掙扎時,最後居然逼出了她以「婚姻」為安頓身心的前提,而朝向「劍道」的境界邁進,不但足以顛覆武俠小說一往情深的「柔情」格局,更提昇、見證了司馬翎筆下女性的獨特的地位--「道」與女性的結合,於此恐怕是「破天荒」的嘗試!在武俠小說女性慣常「被命名」的模式中,司馬翎所賦予女性的「自主性」,實際上無異暗示了「女權」的未來的合理發展。 當然,在此所謂的「女權」,是就女性生命的自主性上說的(這也應該是所有「女權」的一個基點),對女性的競逐權力,司馬翎亦未嘗贊同,但是這不僅是針對女性而已,而是他自身對權力徵逐的反感,男女同例相看。《劍海鷹揚》中,司馬翎將同樣以智慧取勝的辛無痕、辛黑姑母女及端木芙相互對照,正可凸顯出這一點。我們不妨說,司馬翎是武俠小說中難得一見的賦江湖予「女權」的作家,這不僅僅可以從他往往刻意設計隱隱操控著江湖命脈的女性(武功「天下第一」如鬼母冷婀、廣寒仙子邵玉華、魔影子辛無痕;智慧第一如花玉眉、端木芙、紀香瓊)中窺見,更在他對女性生命意義開展的認同中,可以深刻感受到。 司馬翎的重新定位 武俠小說發展的輝煌歷史,是由所有的武俠小說作共同締建的,儘管在小說的文學藝術成就上,個別的差異極大,但是,不可否認的,每一位作家都為此貢獻過一分心力;尤其是台灣,在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尚未能堂堂皇皇引入之前,實際上正是這些向來受到忽視的作家在廣大的讀者群中掀起武俠熱潮。因此,以司馬翎在台灣的影響而言,其地位的重要,是研治武俠文學者不能夠低估的。晚近的研究者由於受到金庸盛名的影響,以金庸經十年修訂後的作品與這些作家未經雕琢的璞玉對比,以致抑揚之際,頗失其實;事實上,金庸在武俠小說上的成就固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金庸儘管優秀,卻無法涵蓋所有武俠作品的風格。金庸於武俠小說誠如五嶽名山,令人高山仰止,但世間的景色,除名山大川外,依然有若干如桂林山水般秀麗的絕境,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司馬翎正如桂林山水,儘管實際文學藝術的成就略遜金庸一籌,但置於梁羽生、古龍之間,則一點都不會遜色,這是筆者個人對司馬翎的評價。 在走過了將近四十年輝煌的歲月後,近十幾年來,武俠小說已經逐漸消褪了它過去無遠弗屆的影響力,究竟武俠小說是否真的將如一些論者所預估的,終將成為明日黃花,事實上是所有關注武俠小說的讀者與作者應該深思的問題。 武俠小說是否還有未來?或者,武俠小說應當如何才能有未來?關於這點,真善美的宋今人首先提出了「人性」的問題 ,其後古龍、金庸亦分別重申此語。的確,武俠小說再如何虛構,所刻劃的江湖再如何虛擬,可是,生活在江湖世界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基上還是擁有各種紛然複雜的人性的「人」,人性的優點與弱點,永遠是小說此一體裁可以發揮的無限空間!不過,一般的武俠小說,在「人」的範疇中,很明顯是以「男人」為主的,寫英雄、寫俠客,總不自覺地以男性為寫照,而忽略了另一性--女人,因此,女性通常只能在武俠小說中充當點綴瓶花的角色,是則儘管寫「人性」,也將是偏頗而不全的。 我們不妨思索,當整個江湖世界都是屬於男性父權意識的投射之際,如果能擷取司馬翎的創作本旨,賦予分量事實上佔得極重的女性以其應有的地位,又將會如何?筆者深信,這將是一種本質上的「新」與「變」,足以重塑一個不一樣的江湖世界,開發出新的武俠小說歷史進程!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司馬翎武俠小說的深刻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
海龟+海螺 
|
|
|

|
|
|
#2 |
|
注册用户
注册日期: Mar 2001
来自: 金沙
帖子: 2,263
精华: 0
|
Up
司马翎的作品值得一读。
__________________
巴蜀缘,一生结 www.luguhu.org |
|
|

|
| 友情连接 | ||||
| 摩托车.上海.中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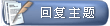



 平板模式
平板模式

